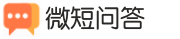尐钕茴亿 1星
共回答了176个问题 评论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①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
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②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儿马③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
这时候,从县城那面,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轱辘滚动的声音,杂着赶车人的吆喝,惊动了牛倌。他望着车上的人们,忘了自己的牲口。前边一头大牤子④趁着这个空,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
①西蔓谷即苋菜。
②长满野草的低湿地。
③没有阉的牡马。
④公牛。
“牛吃庄稼啦。”车上的人叫嚷。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气乎乎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牤子,狠狠地抽了一鞭。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
过了西门桥,赶车的挥动大鞭,鞭梢蜷起又甩直,甩直又蜷起,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马跑得快了,蹄子踏起的泥浆,溅在道边的蒿子上、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跑了一程,辕马遍身冒汗,喷着鼻子,走得慢一些,赶车的就咕噜起来:
“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还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辕马也明白:他只动嘴,不动手,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慢慢吞吞地走着。牲口喘着气,响着鼻子,迈着小步。
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他们通共十五个,坐得挺挤。有的穿灰布军装,有的穿青布小衫。有的挎着匣枪,有的抱着大枪。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他是昨儿给人装柈子①进城来卖的。下晚落在王家店,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他答应下来,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不管好赖,不是空车往回走,能挣一棒子②酒,总是运气。
①劈柴。
②一瓶。
车子慢慢地走着,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老孙头一面骂牲口,一面跳下地来看。轱辘陷在泞泥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他叹一口气,又爬上车来,下死劲用鞭子抽马。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绕到车后,帮忙推车。
这时候,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那赶车的,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因为跑得快,又是胶皮轮,并没有窝住。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手上和小衫子上。那赶车的扭转脖子,见是老孙头,笑了一笑,却并不赔礼,回头赶着车跑了。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悄声地骂道:
“你他妈的没长眼呀!”
“那是谁的车?”十五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问。老孙头瞅他一眼,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车子的萧队长,就回答说:
“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瞅那红骟马①,膘多厚,毛色多光,跑起来,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
“到底是谁的车呢?”萧队长又追问一句。
见问得紧,老孙头倒不敢说了,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②来避开追问。
①骟马即阉马。
②唠嗑即聊天。
萧队长也不再问,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大伙也用死劲来推,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大伙歇了歇气,又上车赶道。
“老孙头,你光打辕马,不是心眼太偏了吗?”萧队长问。“这可不能怨我,怨它劲大。”老孙头笑着说,有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的他的前额上,还有一点黑泥没擦净。
“劲大就该打了吗?”萧队长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奇怪。“队长同志,你不明白,车窝在泥里,不打有劲的,拉不出来呀。你打有劲的,它能往死里拉,一头顶三头。你打那差劲的家伙,打死也不顶事。干啥有啥道,不瞒同志,要说赶车,咱们元茂屯四百户人家,老孙头我不数第一,也数第二呀。”
“你赶多少年车了?”萧队长又问。
“二十八年。可尽是给别人赶车。”老孙头眯起左眼,朝前边张望,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他放了心,让车马慢慢地走着,自己跟萧队长闲唠。
他说,“康德”①八年,他撂下鞭子去开荒,开了五垧②地。到老秋,收五十多石苞米,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他想,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谁知道刚打完场,他害起伤寒病来。五十来石苞米,扎古病③,交出荷④,摊花销,一个冬天,花得溜干二净,一颗也不剩。开的荒地,给日本团圈去,他只得又拿起鞭子,干旧业了。他对萧队长说:
①伪“满洲国”年号。
②一垧是十亩。
③治病。
④出荷,日本话,交出荷即纳粮。
“队长同志,发财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地花个光。你说能不认命吗?往后,我泄劲了。今年元茂闹胡子,家里吃的、穿的、铺的、盖的,都抢个溜光,正下不来炕,揭不开锅盖,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三营,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叫把谷子苞米,通通分给老百姓,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队长同志,真是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咱如今是吃不大饱,也饿不大着,这不就得了吧?吁吁,看你走到哪去呀?”他吆喝着牲口。
萧队长问他:
“你有几个孩子?”
老孙头笑了一笑,才慢慢说:
“穷赶车的,还能有儿子?”
萧队长问:
“为啥?”
老孙头摇摇鞭子说:
“光打好牲口,歪了心眼,还能有儿子?”
十五个人中间的一个年纪挺小的小王,这时插嘴说:“你老伴多大岁数?”
老孙头说:
“四十九。”
小王笑笑说:
“那不用着忙,还会生的。八十八,还能结瓜呀。”车上的人都哗哗地笑了起来,老孙头自己也跟着笑了。为了要显显他的本领,在平道上,他把牲口赶得飞也似地跑,牲口听着他的调度,叫左就左,叫右就右,他操纵车子,就像松花江上的船夫,操纵小船一样地轻巧。跑了一阵,他又叫牲口慢下来,迈小步走。他用手指着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
“瞅那屯子,那是日本开拓团。‘八·一五’炮响,日本子跑走,咱们屯里的人都来捡洋捞①。我老伴说:‘你咋不去?’我说:‘命里没财,捡回也得丢。钱没有好来,就没有好花。’左邻右舍,都捡了东西。有的捡了大洋马,有的捡了九九式枪②,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我那老伴骂开了:‘你这穷鬼,活该穷断你的骨头筋,跟着你倒一辈子霉。人家都捡了洋捞,你不去,还说命里无财哩。’我说:‘等着瞅吧。’
不到半拉月,韩老六拉起大排③来,收洋马,收大枪,收枪子子,收布匹衣裳,锅碗瓢盆,啥啥都收走,连笊篱④都不叫人留。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抗违不交的,给捆上韩家大院,屁股都给打飞了。我对老伴说:‘这会你该看见了吧?’她不吱声。老娘们尽是这样,光看到鼻尖底下的小便宜,不往远处想。”
①发洋财。
②一种日造枪。
③成立地主武装。
④在锅里捞东西用的家什,形如杓子,用柳条或铁丝编成。
萧队长问:
“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
“是咱屯子里的粮户。”
“这人咋样?”
老孙头看看四周,却不吱声。萧队长猜到他的心事,跟他说道:
“别怕,车上都是工作队同志。”
“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怕啥?我是有啥说啥的。要说韩老六这人吧,也不大离①。你瞅那旁拉的苞米。”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这叫老母猪不跷脚②,都是胡子闹瞎的,今年会缺吃的呀,同志。”
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他掉转话头,打听胡子的情况:
“胡子打过你们屯子吗?”
“咋没打过?五月间,胡子两趟打进屯子来。白日放哨,下晚扎古丁③,还糟蹋娘们,真不是人。”
“胡子头叫啥?”
“刘作非。”
“还有谁?”
“那可说不上。”
①差不多。
②形容庄稼长得矮小,猪不用跷脚就能吃到。
③扎古丁即抢劫。
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萧队长也不再问了。他明白,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前怕狼,后怕虎,事事有顾虑。他望望田野,苞米叶子都焦黄,蒿子却青得漆黑。小麦也都淹没在野草里,到处都是攀地龙①和野苇子。在这密密层层的杂草里,一只灰色的跳猫子②,慌里慌张往外窜,小王掏出匣枪来,冲着跳猫子,“当当”给了它两下。他抡起匣枪还要打,萧队长说:
“别再浪费子弹罗,用枪时候还多呢。”
①爬在地上的一种野藤。
②兔子。
小王听从萧队长的话,把匣枪别好。车子平平稳稳地前进。到了杨家店,车子停下,老孙头喂好牲口,抽了一袋烟,又赶车上道。这会大伙都没说啥话,但也没有休息或打盹。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招呼,问长问短,应接不停。工作队的年轻的人们唱着《白毛女》里的歌曲。
萧队长没有唱歌,也没有跟别人唠嗑。他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法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或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时,太早地说到照顾,是不妥当的。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要一场暴风骤雨。
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群众还没动,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那是不行的。可是,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萧队长正想到这里,老孙头大声嚷道:
“快到了,瞅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咱们屯子?”萧队长连忙抬起头,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
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手提一篮子香油馃子①,在道上叫卖。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他连忙跑上,问老孙头道:
“县里来的吗?”
老孙头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扬起鞭子,吆喝牲口往前走。卖馃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往车上看了一阵,随即走开。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拐一个弯,只当没有人看见,撒腿就跑,跑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跟前,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钻了进去。
这人的举动,萧队长都瞅在眼里。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大门用铁皮包着,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灰砖高墙的下边,是柳树障子②和水壕。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黑洞洞的枪眼,像妖怪的眼睛似地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和四围的车马与行人。
长脖子男人推开的小门没有关住,从那门洞里能望到院里。院里的正面,是一排青瓦屋顶的上屋。玻璃窗户擦得亮堂堂。院子的当间,一群白鹅一跛一跛地迈着方步。卖馃子的人跑进去,鹅都嘎嘎地高声大叫,随着鸡也叫,狗也咬,马也在棚下嘶鸣起来,光景十分热闹。萧队长问老孙头道:
“这是什么人家?”
①油条。
②一排丛生的小柳树。
老孙头往四外瞅了一眼,看到近旁没有别的人,才说:“别家还能有这样宽绰的院套?瞅那炮楼子,多威势呀!”“是不是韩老六的院套?”
“嗯哪。”老孙头答应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
这挂车子的到来,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从各个草屋里出来,跑到路旁,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
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车后跑,车子停下,他们也停下。有一个孩子,把左手塞在嘴里头,望着车上的人和枪,歪着脖子笑。不大一会,他往一个破旧的小草屋跑去,一面奔跑,一面嚷道:
“妈呀,三营回来了。”
车道上,一个穿白绸衫子的衔长烟袋的中年胖女人,三步做两步,转进岔道,好像是怕被车上人瞅见似的。
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萧队长从榆树丛子的空处,透过玻璃窗,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他说:
“就住在这行不行?”
大伙都同意,一个个跳下车来,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行李卷往学校里搬。萧队长走到老孙头跟前,把车钱给他,亲亲热热地拍拍他的肩膀,并且说道:
“咱们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回头一定来串门吧。”老孙头把钱接过来,揣在衣兜里,笑得咧开嘴,说道:
“还能不来吗?这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他说完,就赶着车,上街里买酒去了。
19小时前

画半狂 2星
共回答了290个问题 评论
分马
周立波
院子当中摆着一张长方桌子,郭全海用小烟袋锅子敲着桌子说:“别吵吵,分马了。小户一家能摊一头顶用的牲口,领马领牛,听各人的便。人分等,排号;牛马分等,不排号。记住自己的等级、号数,听到叫号就去挑。一等牛马拴在院子西头老榆树底下。”
人们涌上来,围住桌子,好几个人叫道:“都知道了。就动手分吧。”
郭全海爬到桌子上,高声叫道:“别着忙,还得说两句。咱们分了衣裳,又分牛马,倒是谁整的呀?”
无数声音说:“共产党领导的。”
郭全海添着说:“牲口牵回去,见天拉车,拉磨,种地,打柴,要想想牲口是从哪来的;分了东西可不能忘本。”
许多声音回答道:“那哪能呢?”
郭全海说:“现在分吧。”说罢,跳下地来。
栽花先生提着石板,叫第一号。第一号是赵大嫂子。她站在人身后,摇摇左手说:“咱家没有男劳力,白搭牲口;省下给人力足的人家好。”老初和老孙头都劝她要一头,可是她说啥也不要。
第二名是郭全海。郭全海对自己的事总是随随便便的,常常觉得这个好,那个也不赖。老孙头要他牵那匹青骒马,他就牵出来,拴在小学校的窗台旁的一根柱子上,回来再看别人分。
听到喊老初的时候,他早站在牛群的旁边。他早就想要一头牤子,寻思着今年粮食不够,牤子劲大,晚上省喂,不喂料也行,不像骡马,不喂豆饼和高粱就得掉膘。又寻思着,使牛翻地,就是不快,——过年再说吧。他牵着一头毛色像黑缎子似的黑牤牛,往回走了。
老田头走到老孙头跟前,问道:“你要哪匹马?”
“还没定弦。”
其实老孙头早相中了拴在老榆树底下的右眼像玻璃似的栗色小儿马。听到叫他的名字,他大步流星地迈过去牵上。
张景瑞叫道:“瞅老孙头挑匹瞎马。”
老孙头翻身骑在儿马的光背上。小马从来没有人骑过,在场子里乱跑,老孙头揪着它的剪得齐齐整整的鬃毛,一面回答道:“瞎马?这叫玉石眼,是最好的马,屯子里的头号货色,多咱也不能瞎呀。”
小猪馆叫道:“老爷子加小心,别光顾说话,——看掉下来把屁股摔两半!”
老孙头说:“没啥,我老孙头赶了29年大车,还怕这小马崽子?哪一号烈马我没有骑过?多咱看见我老孙头摔过交呀?”
小儿马狂蹦乱跳,两个后蹄一股劲地往后踢,把地上的雪踢得老高。老孙头不再说话,两只手使劲揪着鬃毛,吓得脸像窗户纸似的煞白。马绕着场子奔跑,几十个人也堵它不住,到底把老孙头扔下地来。它冲出人群,一溜烟似地跑了。郭全海慌忙从柱子上解下青骒马,翻身骑上,撵玉石眼去了。这儿老孙头摔倒在地上,半晌起不来。调皮的人们围上来,七嘴八舌打趣他。
“怎么下来了?地上比马上舒坦?”
“这屯子还是数老孙头能干,又会赶车,又会骑马,摔交也摔得漂亮,啪嗒一响掉下地来,又响亮又干脆!”
几个人跑去扶起他来,替他拍掉沾在衣上的干雪,问他哪块摔痛了。老孙头站立起来,嘴里嘀咕着:“这小家伙,回头非揍它不可!哎哟,这儿,给我揉揉。这小家伙,……哎哟,你再揉揉。”
郭全海把玉石眼追了回来,人马都气喘呼呼。老孙头跑到柴垛子边,抽根棒子,撵上儿马,一手牵着它的嚼子,一手抡起木棒,棒子落到半空,却扔在地上,他舍不得打。
继续分马。各家都分了称心的牲口。白大嫂子,张景瑞的后娘,都分到相中的硬实马。老田头夫妇牵了一匹膘肥腿壮的沙栗儿马,十分满意。李大个子不在家,刘德山媳妇代他挑了一匹灰不溜的白骟马,拴到他的马圈里。
李毛驴转变以后,勤勤恳恳,大伙把他的名字也排上了,叫号叫到他的时候,他不要马,也不要牛。栽花先生问他道;“倒是要啥哩?”
李毛驴说:“我要我原来的那两头毛驴。”
“那你牵上吧。”
李毛驴牵着自己的毛驴慢慢地走回家去。后面一群人跟着,议论着:“这真是物还原主。”“早先李毛驴光剩个名,如今又真有毛驴了。”
李毛驴又悲又喜。被杜善人牵去的毛驴又回来了,这使他欢喜;但因这毛驴,他想起了夭折的孩子,走道的媳妇,心里涌起了悲哀。后面一个人好像知道他心事似的,跟他说道:“李毛驴,牲口牵回来,这下可有盼头了。好好干一年,续一房媳妇,不又安上家了吗?”
三百来户都欢天喜地。只有老王太太跟她俩小子没有挑到好牲口,牵了一匹热毛子马。这号马,十冬腊月天,一身毛裉得一干二净,冷得直哆嗦,出不去门。夏天倒长毛,趟地热呼呼地直流汗。她牵着热毛子马,脑瓜耷拉着,见人就叹命不好。
郭全海看到老王太太灰溜溜的样子,走拢来问道:“怎么的了?这马不好?”
“热毛子马。”
郭全海随即对她说:“我跟你换换。瞅瞅拴在窗台边的那匹青骒马,中意不中意?”
老王太太瞅了那马一眼,摇摇头说:“肚子里有崽子,这样大冷天,生下来也难伺候,开春还不能干活。”
郭全海招呼着一些积极分子,到草垛子跟前阳光底下,商量老王太太的事。郭全海蹲在地上,用烟袋锅子划着地上的松雪。对大伙说:“萧队长说过:“先进的要带落后的。咱们算先迈一步,老王太太拉后一点点,咱们得带着她走。新近她又立了功,——要不是她,韩老五还抓不回来呢。要不抠出这个大祸根,咱们分了牲口,也别想过安稳日子。”
老孙头点头说:“嗯哪,怕他报仇。”
郭全海又说:“如今她分了热毛子马不高兴,我那青骒马跟她串换,她又不中意,大伙说怎么办?”
老孙头跟着说:“大伙说怎么办?”
老初说:“她要牛,我把黑牤子给她。”
白大嫂子想起白玉山叮咛她的话,凡事都要做模范,就说:“咱领一匹青骒子,她要是想要,咱也乐意换。”
张景瑞的后娘想起张景祥参军了,张景瑞是治安委员,自私落后就叫他们瞧不起,这回也说:“咱们领的兔灰儿马换给她。”
老田头跑到场子的西头,在人堆里找着他老伴,老两口子商量了一会,他走回来说:“我那沙栗儿马换给她。”
老孙头看老田头也愿意调换,也慷慨地说:“我那玻璃眼倒也乐意换给她,就怕儿马性子烈,她管不住。”
郭全海站起来说:“好吧,咱们都把马牵这儿来,听凭她挑选。”
郭全海邀老王太太到草垛子跟前,答应跟她调换的各家的牲口也都牵来了。老王太太嘴上说着:“就这么的吧,不用换了,把坏的换给你们,不好。”眼睛却骨骨碌碌地瞅这个,望那个。郭全海把自己的青骒马牵到她跟前,大大方方地说:“这马硬实,口又轻,肚子里还带个崽子,开春就是一变俩,你牵上吧。”
老王太太看看青骒马的耷拉着的耳丫子,摇一摇头走开了。
她看了看老初的牤牛,又转转头来瞧了瞧白大嫂子的骡子,都摇一摇头,转身往老孙头的玉石眼儿马走来了。老孙头神色慌张,却又笑着说:“看上了我这破马?我这真是个破马,性子又烈。”
老王太太走近去,用手摸摸那油光闪闪的栗色的脊梁。老孙头在一旁嚷道:“别摸它呀,这家伙不太老实,小心它踢你。我才挑上它,叫它摔一交。样子也不好看,玻璃眼睛,乍一看去,像瞎了似的。”
不知道是听信了老孙头的话呢,还是自己看不上眼,老王太太离开玉石眼了,朝着老田头的沙栗儿马走去。这匹马膘肥腿壮,口不大不小,老王太太就说要这个。老田头笑着说:“你牵上吧。”
大伙都散了。老田头牵着热毛子马回到家里。拴好马,进屋里,老田太太心里不痛快,一声不吱。老田头知道她心事,走到她跟前说道:“不用发愁,翻地拉车,还不一样使?”
老田太太说:“咱们的沙栗儿马膘多厚,劲多大!这马算啥呀?真是到哪里也是个扔贷。”
“能治好的,破上半斗小米,搁巴斗里,入在井里泡上。咱们粮食有多的,破上点粮给它吃就行。”
老田太太坐在炕沿说:“到手的肥肉跟人换骨头,我总是心里不甘。再说,咱们光景还不如人呢。”
老田头说:“你是牺牲不起呀,还是怎么的?你忘了咱们的裙子,她认死也不说出姑爷的事?亏你是她的亲娘,也不学学样,连个马也牺牲不起,——这马又不是不能治好的。”
“是呀,能治好的。”这是窗户外头一个男子的声音,老两口子吃了一惊。老田太太忙问道:“谁呀?”
“我,听不出吗?”
“是郭主任吗?还不快进来?外头多冷!”
郭全海进屋里,笑着说:“我的青骒马牵来了。你们不乐意要热毛子马,换给我吧。”
老田太太的心转过弯来了,笑着说:“不用换了。咱们也能治,还是把你的马牵回去吧。各人都有马,这就好了,不像往年,没有马,可真难呀,连地也租种不上。”
彼此又推让一回,田家到底也不要郭全海的马。最后,郭全海说:“这么的吧,青骒马开春下了崽,马驹子归你。”
16小时前
-
查看 662回答 1
-
查看 580回答 1
-
查看 87回答 1
-
查看 980回答 2
-
查看 40回答 1
-
查看 82回答 1
-
查看 37回答 2
-
查看 508回答 1
-
查看 18回答 2
-
查看 89回答 2
猜你喜欢的问题
-
1天前2个回答
-
1天前1个回答
-
1天前1个回答
-
1天前1个回答
-
1天前2个回答
-
1天前1个回答
热门问题推荐
-
1个月前1个回答
-
2个月前2个回答
-
4个月前2个回答
-
你如何看待孟子所说的夫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子比儿童之是乱 天下也
1个月前1个回答
-
1个月前2个回答
-
3年前2个回答
-
1个月前2个回答
-
1个月前2个回答
-
3个月前1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