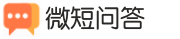赞
赞 儍儍尐孓 3星
共回答了397个问题采纳率:95.4% 评论
1849年,叶名琛在观音山麓修建了一座精舍,取名长春仙馆,作为他已致仕的父亲叶志诜的别墅。叶志诜曾做过内阁中书,既是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也是占卜扶鸾的高手。叶志诜的两个儿子中,长子叶名琛身高一米八0,体态健硕,大脑袋,厚耳垂,一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官相。
叶志诜深信,亲爱的儿子已是举足轻重的国之干城。他要运用他高妙的占扶术,为儿子祈福禳灾,出谋划策。这一年,叶名琛虚岁四十二,已身居广东巡抚要职两年多了。
长春仙馆终日香烟缭绕,这个离休老干部的迎神请仙在这一年冬天为儿子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道光下旨,赏给叶名琛男爵爵位。道光的封赏,源于叶名琛对英人入城事件的处置有方,而英人入城事件的起因,则要追溯到几年前的鸦片战争。
众所周知,中英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就是《南京条约》。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条约中真正侵犯中国主权,对中国具有杀伤力的是割地和赔款,而另外的诸如五口通商和允许英人进入通商口岸,反而无足轻重,或者说相对平等。但是,令后人看不懂的是,清朝痛快地割了地赔了款,却对英人进入通商口岸阳奉阴违。
当福州、上海、宁波和厦门已依约设立领事馆,洋人也在城内改建或是租赁了房屋时,最早与洋人接触的广州,包括英人在内的所有洋人,统统被限制在城外的商馆及其房前屋后狭窄的花园里。
当他们按条约规定提出入城要求时,广州民众坚决反对。为此,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向英方推诿:广东民风剽悍,民间反应过激,还是过两年再说吧。英方只好答应了。
两年后,当英方来找耆英兑现承诺时,两广总督已换成了徐广缙。两广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他和叶名琛。这两个负责人一致认定,同意英人入城有百害无一利。并且,倘若阻止英人入城的话,还将获得民众的大力支持――此外,更在于他们吃准了远在北京的道光的心思:这位以天下共主自居的皇帝,骨子里并不打算兑现条约。或者说,他希望尽最大可能的爽约。
于是乎,一场由官府发动,却号称民间行为的抵制英人入城运动拉开帷幕。卫三畏在广州做编辑,恰逢其盛,他对斯时的情况写道:“身着号衣,手执长矛、火炮和滑膛枪的百姓开始在晚上沿街列队行进。可能有一万人应召入伍。”
英方没想到两年的等待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结果。生气归生气,却也只得暂时中止入城,背地里,再积极寻找突破口。而清朝上下,则把英人的隐忍看作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广州城里,绅民搭起了六座宏伟的牌楼,敲锣打鼓地为徐、叶二人庆功。道光也下旨说,这是与洋人打交道十余年来,最令他痛快的事。是故,龙颜大悦之余,叶名琛赏男爵,徐广绅赏伯爵。
在我们今天看来,英人到底进不进入广州城,其实无关宏旨。但在清朝上下,却无不以为暂时地阻挡了英人入城,乃是一场了不起的大捷。这其中隐含的前提就是:哪怕几年前才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打,但固执的清朝仍把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而天朝上国,自然不愿夷狄之人进入自己的国度,与自己的国民摩肩接踵。这样既有伤风化,也有辱国格。
英人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如此古怪的观念,很自然地,就把它视作清朝背信弃义。他们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叫做祖制与国体的东西在这个老大帝国体内起作用。在这个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老大帝国,无论多么琐屑的事情,只要一旦和祖制、国体相勾联,就成了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头等大事。
当英人因兵力不济,暂且停止进入广州城时,清朝从官方到民间,都沉浸在胜利的迷醉中。这场虚无缥缈的胜利,让咸丰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也让叶名琛捡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男爵。
与此同时,叶名琛也被朝野上下看成是最懂洋务,最善于忽悠洋人的能吏和可以向洋人说不的民族英雄。这一切,就像他的一个朋友在写给他的信中吹捧的那样:“经文纬武,帝资为海国干城;宣德布威,众仰为人间山斗。”
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叶名琛和洋人打交道时,他总是胸有成竹。他以为他拥有胸有成竹的资本和经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叶名琛肯定会被定性为和林则徐一样伟大的民族英雄。然而,叶名琛的运气似乎要比他的前辈林则徐稍微差一些。
几年过去了,叶名琛已升任两广总督,同时兼任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这一年,英国全权公使包令走马上任。包令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与负责外交的叶名琛会谈。叶名琛对与包令会谈倒并没意见。问题是,他认为,两人的会谈地点只能选择洋行的贷栈或是虎门码头,总之,只要不进广州城,其它地方都好说;而包令则坚持必须进城。――显然,二人会谈地点之争,仍然是英人入城之争的翻版。
这事放在今天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人家既然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节,你是负责大清外交的官员,为什么就不能让人家进你的城呢?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这不可思议,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承认了各个国家之间都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
但在叶名琛时代,儒家酱缸里浸染出来的清朝君臣,他们固执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再多,其实也无非两个,一个是他们的天朝,另一个则是其它国家。大清与其它国家之间,只可能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或是天朝上国与夷狄之邦的关系,绝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一旦默认其它国家的使节入城,甚至其它国家的民众也入城,那无疑就是在天朝和其它国家之间划上了等号,孰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哪怕洋人已经进入了其它四个通商口岸,但只要争得广州一地的“纯洁”,也算是为帝国保住了最后的贞操和颜面。这样,包令和叶名琛之间的交涉,就注定了是鸡同鸭讲。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英国绅士慢慢开始相信,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达到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就在包令打算带一支舰队北上时,天赐良机,上天给了英国人一个绝好的出兵机会,那就是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原本是一只普通商船,在香港注册,船主和船员都是中国人,相当于今天那种戴外资帽子实则国人经营的假外资企业。其意图,不外乎挂了英国国旗,走私时胆子更大一些。这只涉嫌走私的商船被清军水师扣押,船员被逮捕,英国国旗据说也被清军拨起后扔到甲板上。巴夏礼闻讯赶来,被清军的一个水手在激愤中打了一巴掌。
事情就此闹大了。此时包令已改任港督,由巴夏礼代理公使一职。巴夏礼要求叶名琛释放船员,并向英国道歉。释放船员事小,道歉却事关国体,叶名琛坚决不同意。这样,包令和叶名琛之间就通过第三方传话的方式展开了一场论战。
论战还没结果,英国方面可能觉得包令太过婆婆妈妈――事实上,包令既是英国政府雇员,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懂几十门语言的大学者,骨子里有着文人和殖民官员的双重性格。
为此,英国宣布另外委任额尔金为特命全权公使,负责处理和清朝的争端。情况急转直下,可惜的是,清朝上下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在叶名琛看来,对付英人的最有效办法,仍然是此前阻止他们入城的老套路。
在额尔金率领舰队抵达广州之前的1856年十月,英军攻占腊得中流炮台。当时,叶名琛正在较场举行武举射箭考试,炮弹就落在他身旁不远的地方。左右相顾失色,叶名琛却笑着说,没事,到了日落时分他们就退了。当天,英军以数百人之众,很快攻陷了广州城,并焚毁了总督衙门。旋即,因人数太少,果然在日落时分撤到城外。
英军的进而复退,原本是兵力不够,或者说暂时还没有全面升级战争的想法,只不过想给叶名琛一点颜色,希望他回到谈判桌上,让双方以平等的而非天朝与夷狄的礼仪谈判。但是,不仅叶名琛误解了英国人,民众和官员也都集体误解了英国人――他们把英军的撤退,说成是英国不敢跟大清玩真的,不过是吓唬人罢了。
坊间流言纷传,要么说英国国主根本不准备对天朝用兵,这都是包令和巴夏礼的个人行为;要么说英国正与俄罗斯激战,连殖民地印度都起来造反了。总之一句话,敌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再联系到几年前民众成功阻止英人入城,广州城里群情激动。
民众一旦激动起来,就会像一把突如其来的大火:在官府的默许下,民众烧毁了所有和外国人相关的建筑――从十三行的贷栈到英国的领事馆,乃至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居所。
当是时,大清境内正是民变风起云涌之时,太平天国、天地会和捻军如火如荼,官府对民众的高压和民众对官府的不信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对抗英国人这一点上,官府和民众却惊人一致。
自叶名琛以下,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民心可用――于是乎,民族情绪被无限地放大了,而被放大的民族情绪往往会干下难以收拾的蠢事。从这种意义上讲,广州民众焚毁外国使馆和居所的行为,正是多年以后义和团运动的热身。
但叶名琛们是看不清楚这一点的。历史的残酷就在于,许多后人一目了然的道理,身处其中的当局者却永远不会搞明白。英国人主动退兵,叶名琛向咸丰汇报的却是一次虚构的大捷。被太平天国弄得焦头烂额的咸丰闻讯,高兴得合不拢嘴,更加相信他在几年前的圣旨中的判断:有了叶名琛这样的能吏,就能做到“中外绥靖,可以久安。”
无疑,1856年的广州是全中国最和谐的地方:当受太平天国影响,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朝廷四处派兵征剿之时;当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陷于内讧,自相残杀之际;广州民众与官府却罕见地步调一致。这种神奇的和谐来自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并通过这个共同的敌人,寻找回了一种可疑的自信。这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被民众和官府一致认为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的英国人。
然而,额尔金率领舰队赶来了。尽管此人乃一不折不扣的鹰派,但他一开始仍没打算动武。他派人向叶名琛提议谈判,谈判的内容不仅包括英人入城,还包括十二年期满的《南京条约》的修约。
但叶名琛绝不会和英国人谈判――他的自负既来自于自以为此前两次和英人的交手都占了上锋,因而根本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同时更在于,当时的广东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要仰仗广东。道光和咸丰两任皇帝都曾多次告诫叶名琛,和洋人打交道要谨慎,千万不能出乱子,以免响财政。
叶名琛为了显示自己能干,此前送往北京的报告,无一不是报喜不报忧,以致咸丰曾经指示说,平时给夷人一点小教训就是了,等他们主动承认了错误,我们天朝上国,还是要给人家台阶下的。如此一来,叶名琛岂敢再和英国人谈判?更何况谈判的内容是天朝极为敏感的《南京条约》。
因此,在和洋人的交往中,叶名琛接到洋人的文书后,要么不置一词,要么三言两语如同领导训话。与其把这完全归之于叶名琛的自负,不如说主要是驼鸟心态在起作用。在叶名琛这种对世界缺乏最基本了解的官员意识里,只要闭上眼睛,天底下就永远不会有悬崖。
额尔金一度打算绕过叶名琛。但当他和其它省的清朝官员交涉时,其它官员避之惟恐不及,根本不趟这浑水。当他想和清朝中央政府交涉,可天朝大国除了理藩院这个办理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外,并没有其它的外交机构。额尔金家族一直在英国海外殖民地做官,他本人就曾做过牙买加总督和加拿大总督,可他以往那套国际通行做法一旦拿到清朝,通通水土不服,压根儿行不通。
不可否认,在中英的博奕中,英国的确是侵略者。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强凌弱那么简单,其最本质的差异在于,侵略者在签定了和约之后,打算按照国际惯例去遵守。和约自然有失公允,但真正有失公允的割地赔款,清朝已经照办了。反倒是公允之处,如五口通商、英人进入口岸,清朝却无端纠结。
其中最核心的症结在于,当时光已经迈入近代,全球逐步走向一体化时,从长白山老林子里骑马射箭得天下的清朝君臣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几个世纪以前: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现代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理解为儒家视角下的正朔与夷狄的关系。即便是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样的国际条约,也仅仅只是被他们看作不得已时用来羁靡夷狄的缓兵之计,相当于历史上的岁贡之类的玩艺儿。
打一开始,清朝就不准备遵守和约。一旦有机会,还会千方百计破坏它。对已经进入近代化的英国来讲,他们最不能理解、或者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点。
额尔金终于暴跳如雷,他失去了继续和叶名琛打口水仗的耐心。1857年11月12日,额尔金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谍,限叶名琛二十四小时内投降。此时,战争已成必然。然而,当部属们请求叶名琛积极备战时,叶名琛却坚决不许。他说,先等着,过了十五,必然就没事了。
他之所以如此胸有成竹,原因有两,其一,他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只是额尔金背着英国国王的擅自行动,乃是虚张声势,根本不可能真打起来。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像之前阻止英人入城那样,用一个拖字诀,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二,他那个精通占扶的父亲在长春仙馆里为他扶乩得出了结论。
长春仙馆里,出人意料地供奉着两个仙人,一个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一个是唐代大诗人李太白。叶志诜老先生的扶乩看来的确很准:过了十五的确没事了――因为,英军十四日就攻陷了广州,并把企图翻墙逃跑的叶名琛俘获。俘获时,这个所谓的民族英雄吓得浑身发抖,拒不承认他就是两广最高首长。不过,一旦巴夏礼使他相信自己生命无虞后,他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傲慢。
当咸丰在紫禁城里接到叶名琛被俘获的消息时,丈二尺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叶名琛不是说英国人头脑简单,很好忽悠,早就被我们搞定了吗?
关于英军进攻广州的情景,《泰晤士报》中国特派记者柯克做了生动的描述,从他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叶名琛之辈的颟顸和普通民众的麻木:
“仍然没有投降的迹象。这些奇怪的中国人看来已习惯于此。舢板,甚至货船像伦敦驳船一样在河上行驶,照旧停靠;百姓到岸边,注视飞过他们头顶的炮弹……距‘费勒吉敦号’200码内,一户人家在临河的房间内吃晚饭,而此时‘费勒吉敦号’还在不断发射,炮弹在他们头上几英尺处飞过。炮火明亮,屋内纤微悉见;屋内的人照样吃饭,好像外面没有发生什么事……我听说,尽管没有亲见,舢板整天一直从一艘船划到另一艘船,向正在炮击省城的水手售卖水果蔬菜。谁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此后事态的发展已经写进了中学历史课本:英法联军直逼京城,咸丰逃往热河。然后,联军进城,一把火烧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额尔金的父亲老额尔金在希腊曾洗劫过台帕农神庙,额尔金则毁了圆明园,父子俩的作为,倒是十分相配。
再然后,咸丰命恭亲王奕䜣与联军谈判。谈判的结果不仅英法得到了巨额赔偿和其它好处,就连美国和俄国也跟着沾光,单是俄国,就从中国搞到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惟一正面的结局是,此前坚决不愿和夷人平起平坐的清朝,终于放下身段,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后,额尔金们再也不会为找不到可以谈判的机构怒发冲冠了。
叶名琛以总督和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作了俘虏。咸丰担心他被英军用作要挟的人质,事发之后,不仅没出面营救,反而宣布免去他的一切职务。英军押送叶名琛由舢板登上军舰时,叶的手下以手指河,向叶递眼色,示意叶名琛投河自尽,以全名节。但是,叶名琛不知是没看见还是没领会,他一言不发地登上了英国军舰。
如此高官被俘,英国人倒也没虐待他。他在军舰上生活了48天,其间,据《香港纪事报》载,军舰上的所有军官都很尊敬他。偶尔有人上舰,都向他脱帽致意,叶名琛也欠身脱帽还礼。
次年春天,英军把叶名琛押送到了殖民地加尔各答。一年之后,叶在异乡病死。囚禁期间,叶名琛每天做的事就是写诗、绘画、背诵《吕祖经》。有不少洋人曾向叶名琛求字画,叶名琛一律不署真名,只署海上苏武。
关于叶名琛的死,除了病逝之说外,还有所谓耻食英粟,绝食而死的记载。这一记载的真伪与否暂且不论,但即便死得如此慷慨激昂,也并不能挽回他此前铸成的大错。正是他的昏聩与固执,愚昧和迷信,才导致了英法联军的武力北上,并叩开紫禁城大门。
叶名琛的绝食而死,至多只能说他在人品上还不算太糟糕。或者,更极端地说,当他明白此前的行状已足以使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他惟一可以稍微洗刷耻辱的机会就是高调地死、大义凛然地死。这样,或许可以给他带来死后的名声与气节。虽然这名声与气节,对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于事无补。
叶名琛生于1809年。叶家几代人以来都以读书入仕为业,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这样的家族是最令人艳羡和视为正途的。当叶名琛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只有二十六岁。即便用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来要求他,他也算年轻有为。
此后,叶名琛任过多种职务的地方官,他的升迁速度令时人侧目。当他出任副省级的云南按察使时,虚岁三十三,升至正省级的广东巡抚时,区区三十八。清朝尽管腐败,但在官员的升降考核上,却还是靠实实在在的政绩说话。这种火箭式的升迁,对一个并没有多少政治背景的地方官员来说,只能说明一件事:他是个能吏。正如他的家乡汉阳所修的县志上称赞的那样,他“所至兴利剔弊,察吏安氓,口碑溢数省焉。”
当叶名琛成为独挡一面的方面大员时,正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风起于青苹之末时。广东地近起事的广西,一方面守土有责,另一方面,因广东富庶,还得为国家负担大量军饷。自太平天国起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的军饷以白银千万两计,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
太平天国起事后,没有顺着珠江进入广东,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叶名琛的严防死守,但至少也有一定关系。受太平天国影响,广东境内曾爆发天地会起义,叶名琛作为最高官员,负责了整个剿杀行动。咸丰四年的红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却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不仅守住了广州城,还将红兵驱逐出境。
如同历代政府对农民起义的围剿一样,手段总是极为残忍血腥。在广东红兵变乱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有时一天竟然屠杀俘虏上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855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当是时,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容闳目睹了这种血腥的屠杀。
衡量以今天的标准,叶名琛如此嗜杀成性,视民命如草芥,自然罪不容诛。但站在彼时的立场上,造反本身就是灭族的大罪,至于叶名琛滥杀无辜,也不过所谓宁可枉杀三千,绝不可放过一个的注脚罢了。
然而,为何一个如此能干,如此深得两朝天子信任和器重的封疆大吏,一旦与外国人打交道,就变得不可思议的愚昧和不堪呢?
显然,是这个古老而僵化的帝国积重难返的观念导致了叶名琛成为宿命的奴隶。尽管鸦片战争中,清朝已尝到了洋人的厉害。但当其时也,这个古老国度的君臣们,其骨子里,仍然把它当作了一次偶然。还要等上好多年的光阴,他们的后代才会明白,古老东方僵化的祖制和国体,早已跟不上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以英人入城为例,它既是此前《南京条约》中的一款,同时也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但高高在上――其实是自欺欺人地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大清君臣,却坚持所谓夷夏之大防,宁肯割地赔款,也不愿英人入城。一旦英人迫于民众压力暂时退却,则又无限膨胀,以为民心可用,有了和英人叫板的底气。
一言以蔽之,如果清朝君臣能认识到当时的国际气候,理智地遵守此前签订的和约,哪怕这和约有不平等之处,但也绝不会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因争一时意气而使事情愈发不可收拾。换句话说,哪怕是充当受害者,也得遵守游戏规则。一旦不遵守游戏规则,吃大亏的还是自己。
叶名琛的误国,被时人讥为六不总督,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是也。其实,叶名琛战也好,和也罢,守也好,走也罢,都不足以改变他的宿命。若选择战,那么为了皇帝的脸面而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就是先例;若选择和,那么撤职查办,锁拿进京的琦善就是前车。
所以,在这样一种祖制之下的高级官员,其实就是宿命圈定的奴隶。无论是慷慨激昂的主战派,还是忍气吞声的主和派,乃至不战也不和的驼鸟派,都注定只有一个结局:身败名裂。
因为,在一个天崩地坼的巨变时代,身败名裂将是无数帝王将相的共同下场。
11小时前
-
查看 42回答 1
-
查看 902回答 1
-
查看 938回答 1
-
查看 110回答 1
-
查看 61回答 1
-
查看 366回答 1
-
查看 58回答 6
-
查看 69回答 1
-
查看 872回答 1
-
查看 910回答 1
猜你喜欢的问题
-
16天前1个回答
-
16天前1个回答
-
16天前2个回答
-
16天前4个回答
-
16天前1个回答
-
16天前1个回答
热门问题推荐
-
3个月前2个回答
-
3个月前1个回答
-
3个月前1个回答
-
3个月前2个回答
-
1个月前2个回答
-
1个月前1个回答
-
1个月前1个回答
-
3个月前1个回答
-
2个月前1个回答